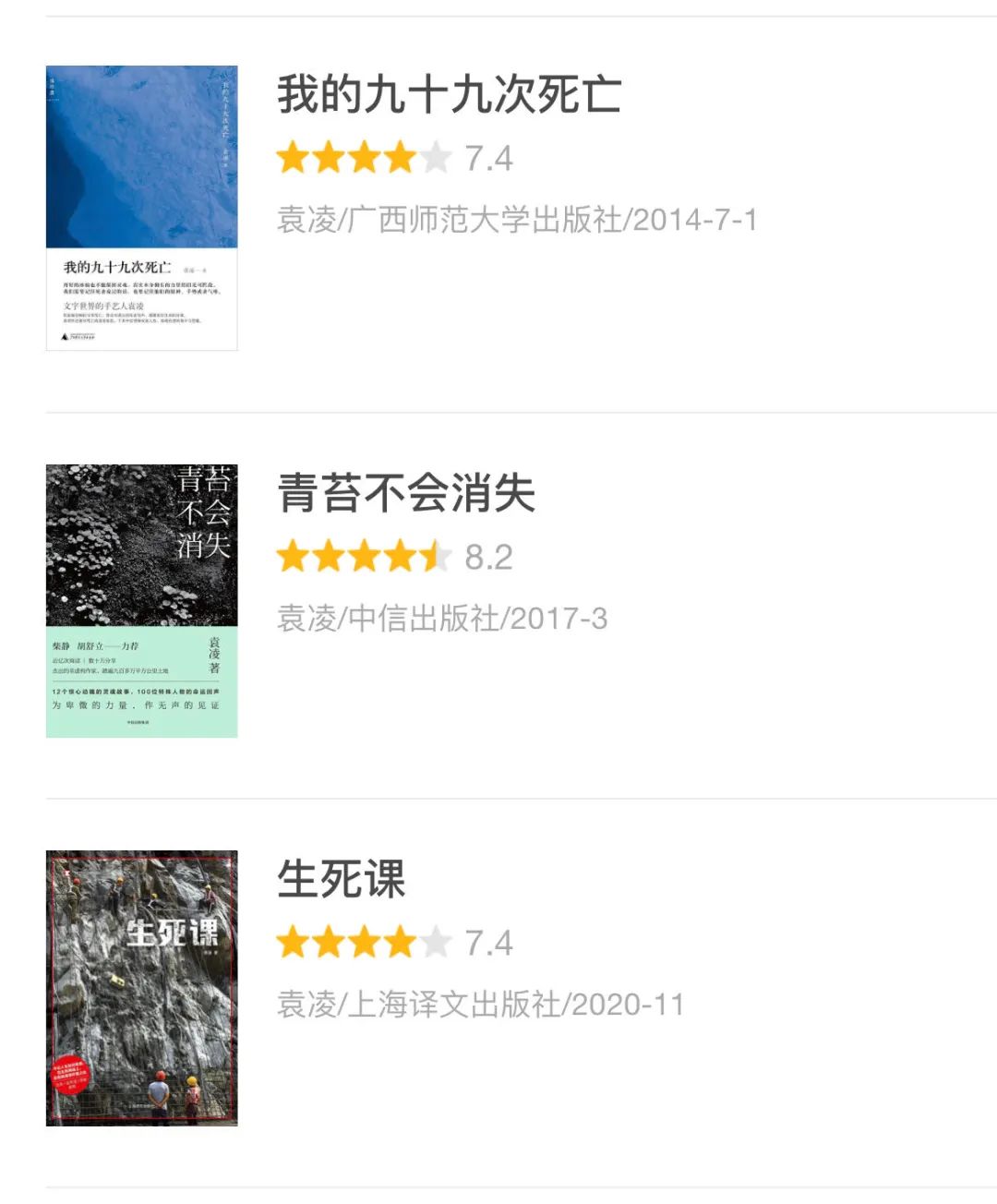播客|血矿·枭雄·病人:袁凌谈中国矿工往事
来源网站:mp.weixin.qq.com
作者:忽左忽右Leftright
主题分类:劳动者处境
内容类型: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
关键词:矿工, 尘肺病, 粉尘, 煤矿, 矿难
涉及行业:采矿业
涉及职业:蓝领受雇者
地点: 陕西省
相关议题:工伤/职业病, 肮脏或危险的工作环境
- 矿工在极端危险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劳作,面临尘肺病、砷中毒等职业病的高风险。
- 矿难频发,矿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得不到有效保障,死亡或残疾的赔偿远远低于其生命价值。
- 矿工的劳动条件极其艰苦,安全设施缺乏,工资低且工作时间长。
- 繁峙矿难后,死亡赔偿标准提高,对矿业安全管理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。
- 湖南石门县雄黄矿的环境污染严重,导致大量矿工和当地居民患上癌症,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。
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,仅供参考,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。
本期介绍
预计阅读10分钟
作家袁凌从小在煤矿边长大,他说矿有时是资源,有时也是一种诅咒。回到二三十年前,他在奔腾的矿业里记录下白手起家的风云往事,不乏繁华一时的大矿与大厂,但更多的是在地下千米深处赤身裸体的工人,扛着高温与粉尘,在黑暗的矿壁之间用青壮年的血泪换钱。袁凌在采访和亲身经历中目睹了无数矿业中的死亡与被尘肺病、砷中毒、残疾所折磨的矿工。矿难报道中的一个个数字背后是怎样的故事,地下数千米又是怎样一个世界,欢迎收听袁老师的精彩分享!
内容节选
本文为基于节目录音的口述稿,仅对语法与用词做部分修改。
袁凌家乡陕西安康有悠久的矿业历史
袁凌
我们家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煤窝子,到处都是农民自己偷偷去开一个洞,挖一些煤出来。我小时候典型的记忆就是披星戴月的晚上,我跟我妈妈、我哥、我姐一个人背一个背篓,翻过两座山到一个洞里面,没有任何的安全设置,就一个楼梯搭下去,我不知道他们往下爬多深,我一个人待在外面,(他们)不让我下去,天地都是黑的,我恐惧的不得了。他们把一背篓一背篓的煤偷出来,因为怕被人发现,那个时候煤矿是国家的矿产,而且国家确实在我们队上开了一个矿,所以这个都算是偷煤。
程衍梁
所以算是官营的矿,但是有很多人去打了洞。
袁凌
因为它有个主向道, 1 号井、 2 号井,这是横井。但是对于农民本来就是千百年都烧,凭什么不让我烧?就偷偷在山上打竖洞下去。就是这么一个小时候的典型场景,其实很难忘的。
程衍梁
那是什么年代?
袁凌
......70年的中后期到80年的初期都那个样。这是一个典型的场景,另外的一些场景很惨烈。比如说有一次回家听到说出了矿难,一下子死了七个人,都是我们队上的大人,是那些主要劳动力。跑过去家长也不让小孩子凑得很近,就远远地看着。我有个特别深的印象,这些人出来以后,他好像很平静地躺在那里,有点像睡着了,但尤其是他们的耳朵跟一些煤矿的坑木挨得很近,那些坑木上又长了一些蘑菇,你就感觉他们的耳朵好像也是蘑菇一样。我小时候就是这种印象特别强烈。他脸上有那些红红白白的,可能有鲜血、有脑浆什么的,都不敢细看。总之就是这个感觉,他们就像长出了蘑菇一样。
很多年以后我把这个故事写在《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里面》。这是挺吓人的,那时候太小了,来不及理解这个悲剧有多深,这个事情有多恐怖,后面意味着什么。它就是一次冒顶事故,就塌下来了。
我表哥带我进过那种矿,我真的被震撼了。山里面都挖空了,走廊很深,好几公里长,安全设施非常差劲,可能有一小截是用木头支撑着,到里面干脆就没有那个东西了,就是挖出来的洞,可能它直立性比较好。然后有很多岔洞,你根本就会迷路,矿车呼呼呼就过来了,那个场景我真的终身难忘,因为我当时真的很小,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。
金矿与煤矿:钻机带来尘肺病
程衍梁
你看改革开放之前,甚至自古以来,这种官营的煤矿都存在,这是古老的行业。但以前是不是也没怎么听说有尘肺病这事啊?
袁凌
我想是有几个原因,一个是以前人他不知道这个东西。以前没有钻子,我想这是最关键的东西。没有这种东西它就不足以引起大量的粉尘。
以前最多就是炸药跑一跑,打洞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高效和剧烈。钢钎子慢慢打,那个东西没多大粉尘,后来都是用爆钻机的。你快速地打洞,粉尘就特别的大。所以我想为什么以往没有(大量尘肺病)这个东西,可能就是由于机械并不够先进。
程衍梁
可能很多人觉得当了矿工就很容易得上尘肺病,但我之前也跟你线下交流过,好像也不是这么一回事。是一些特定的工种会爆发尘肺病。
袁凌
对,因为矿里面分几类工种,每一类工种的工作环境是不一样的,譬如说这个你只是一个渣工,渣工是运煤的,是吧?
程衍梁
没什么技术含量。
袁凌
没有技术含量,但是反而危险小,因为程序是先打钻,打钻的时候由于高速运转的钻头要打洞出来,就跟那个我们打墙一样,粉尘是非常大的,大到你对面两个人根本看不见。我在金矿里看他们打钻就是这样,根本看不见彼此。这就是粉尘最浓的时候,等到打钻打了以后,开始装药,装药以后开始放炮,炮放了以后那一会儿也是很大的灰尘,但是等到渣工进场的时候,粉尘已经散了一部分了,所以你还是有可能染上尘肺,但是可能性就小很多了。
程衍梁
不算最危险的了。不过渣工应该属于那种拿的钱确实也很低。
袁凌
他的工作时间最长,工资最低。
程衍梁
也很累。但反过来幸运的一点就是尘肺的概率更小一点。
袁凌
这个当然还要分两种情况。煤矿的风险比金矿小,因为煤矿很多时候它是伴生着水的,有水的话一边打钻的时候,一边同时有水去冲,这样就能把粉尘压住。但是金矿很多时候它是没有水的。金矿跟水伴生的比例比较低,一般情况下是没有水的,因为金矿的矿脉它不是沉积性的,或者说它跟煤矿的沉积原理不同,因为我们知道煤矿是一些树、树叶,它一般是湿润的。我们家乡的煤都是这样的。金矿一般都是干的,而且往往在很高的山上,你根本拉水都拉不上来,所以它环境的粉尘就很大。
繁峙矿难抬高“命价”
袁凌
当时有一个要命的、特别不合理的现实,就是矿工的命贱如草芥,赔偿的价格低到惊人。一个矿工死了,他只值几千块钱。一个矿工浑身瘫痪的,比如我采访的《血煤上的青苔》里面截瘫的胸部以下动不了了,才补了他4,000块钱。
程衍梁
这个是谁来补?
袁凌
包工头。这些包工头一般来说都是他们的亲戚,还有是同村的老乡。比如说过年了,我有点人脉,带几个人出去,这几个人就算我的。这个人出事就找他,他再找上面的人,带班的找跑井的,跑井的找分包头,分包头又找大包头。所以最后这个人死了之后,落到这个矿工手上的命价就只有几千块钱。
程衍梁
这中间应该也有层层抽水的。
袁凌
我觉得是有可能的,就是大包头给中间,中间再给带班的、跑井的,一层层地拨下来,就一点点。最高的——真的有亲戚关系的那种——也就是一两万,一般来说都是一万以下,所以说人命贱到那种程度。正因为人命贱,老板他也不怕。你死人就死人嘛,我就赔那么一点,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,根本不在乎死多少人。矿难遍地开花。我刚到《新京报》的时候真的天天都是这种东西。
那是03年左右。03年发生的一个很大的事件,繁峙矿难,就是我们平利人长期占据了显赫工种的山西繁峙金矿。(这个矿难)很恶劣,因为它死的人多,有一百多个人。第二是那些人死了之后它瞒报。以金国宗为首(的人)帮矿老板转移尸体,转移以后甚至焚烧,一部分掩埋一部分焚烧,毁尸灭迹。后来被报道出来了,把这些被焚尸的、被掩埋的、转移的都找出来以后,在现场视察的高层领导震怒。当地矿工,各种开矿的那里有三万人,一夜之间都被遣散了,整个山西的矿业都停产整顿好几个月,好像是半年。然后出台了一个划时代的政策,要让矿老板赔得倾家荡产,不能再让矿工的命这么贱了,(死亡赔偿)标准一下子提到了30多万以上一个人,后来慢慢地达到上百万一个矿工,那就跟过去完全是不是一回事了。
程衍梁
就他强迫你要去强迫你(注意)安全。
袁凌
对,因为价格高了,你死不起人。你以前死100个人,死10个人都不当回事,现在你死一个人可能都要赔了。这真的是一个决定性的,同时就是查瞒报,安监局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,所以后来慢慢地矿难就减少了,这是一个原因。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整个这个中国的资源配置发生了变化,煤不再那么紧俏了。
湖南石门雄黄矿与它的环境诅咒
袁凌
湖南有一个雄黄矿,副产品是砒霜。
程衍梁
它也算是国营的一个老厂吗?
袁凌
它从清代就有了,民国的时候就已经是个大厂了,建国以后就是一个很大的矿。它是一个很大的国营厂,但国营厂因为有编制的工人是不够的,所以它总是在当地招临时工人。临时工人就给他一个临时工的钱,他也不用负很多的责任。(这个厂)主要的问题既不是矿难,也不是尘肺病,就是大批的癌症死亡,因为砷中毒,就是砒霜。你去看它的矿石上面都是白花花的东西。
程衍梁
就把土壤给污染了。
袁凌
一个是接触,他们开矿的时候直接接触这个矿石。第二个当地的土壤、河流都是有毒的。在河里面洗衣的人,后来手上都是烂出骨头来,溃烂成白骨。那个土地,别说土地有毒了,它结的果子你都不敢吃,含砷量嗡嗡的。那边毒到蚊子都比外面的蚊子要毒得多,因为那个地方幸存下来的蚊子已经是熬练出来了,本身就含有很大的毒素。我记得我在那里,被咬一口以后起多大的包啊。那个地方已经整个被诅咒了,中毒了,死亡量太大了。
程衍梁
在湖南哪里啊?
袁凌
湖南石门县,我看他们的统计数据每年能死到三四百个人,后来高峰期死到六百多个人。你看这样他累积下来几十年就是一万多人都死在砷中毒上面。都是癌症。我在《砷冤的赎价》里面写它就像开花了,先是发炎,后来直接就开花了。
程衍梁
什么叫开花?
袁凌
他伤口溃烂以后又变异,就像癌细胞它不是那一种变异嘛。变异以后它生长成一种很奇怪的,很狰狞的花朵。
还有一些鱼鳞一样的皮肤特别痒,不停地抠,还有可能内脏坏掉了,肝衰竭,呼吸困难。比如我见到一个人,他躺在椅子上,用制氧机维持生命,就跟尘肺病人一样。他就有气无力地对我说,我人吃亏得很呐,就是难受湖南人叫吃亏。没过多久我就知道他死了。还有一个人是鱼鳞病,不停地抠,也是过了半年他就死了,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不知道多少人了,几十年当中多数人都已经死了,但是还有人继续在死。
到了90年代以后,因为污染实在太大了,灾难太严重了,就把矿给关了。但关了之后没有办法一下子处理,因为那个环境是毒化的,土壤、水都是毒化的。第二个以前这些人中的毒慢慢地显现出来。第三个他虽然把那个矿封了,但是那个里面有水,水从矿里面流出来,看起来就是红的、黄的,它仍然是高度的污染。那些人又迁不走,外面没什么安置政策。
好多人老了,根本就迁不动。还有小孩在上学。我去的时候每天上学放学看到很多孩子,所以说他仍然是在延续。当地公益组织想给他们弄一点钱、药给他们去砷,但也没多大用。那些人就说你别给我治了,你把钱给我,我买点好吃的,反正我吃两顿好的,死了就算了。
确实也就是这样,成年累月地沉积在里面,他其实没有救的,你看到那种场景的时候觉得确实很惨烈。尤其是你看到以往的那些(死亡)数字,哪一年哪些人都没有名字,就数字,一个个的数字,就这样死。而且那个地方曾经一度很繁荣,它有条街号称小香港,五脏俱全,大礼堂、电影院、跳舞的呀,各种各样的幼儿园、游乐设施,那个时候很繁华。
程衍梁
我觉得这真的是典型时代国营大厂的那种痕迹。
袁凌
非常繁华,外地客商来那种宾馆,还有当地的一些VCD,你看到那些人在上面表演节目欣欣向荣,但实际上就是一边是开始大面积死亡,一边还在给你弄,后来就繁华一梦,落幕之后就是遍地的死亡,建筑都蒙上了灰尘,都已经千疮百孔,山上一层一层的坟。所以矿有时候是一种很好的东西,但也很可能变成灾难的冤首。
程衍梁
确实是。听起来既像一种资源,又像一种诅咒。
本期嘉宾
程衍梁(微博@GrenadierGuard2)
袁凌,独立作家
本期提到
点击文末“阅读原文” 查看本期豆列
《我的九十九次死亡》 / 《首富之死》 / 《青苔不会消失》 / 《砷冤的赎价》 / 《生死课》
👂🏻
文稿、排版:EMMA
编辑:hualun
播客|被剥夺的童年:留守儿童、边缘群体与全社会的创伤